最佳答案
编者按:又是一年开学季。大一新生们在开启大学生活的欣喜之余,对于所学专业或许还比较陌生。如何快速进入专业,学习相关知识,对学科形成全面的系统认知?中国
编者按:又是一年开学季。大一新生们在开启大学生活的欣喜之余,对于所学专业或许还比较陌生。如何快速进入专业,学习相关知识,对学科形成全面的系统认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特别推出系列讲座,邀请历史学、哲学、传播学等专业的专家学者,分享专业知识、入门技巧,希望学子们上好“开学第一课”,尽快进入状态,拥抱丰富多彩的人生新阶段。该系列讲座首播于B站,由B站相关up主担任主持人,经授权,澎湃新闻·思想市场择其精要整理成文。本文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刘海龙、讲师董晨宇谈传播学,内容已经主讲人审定。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刘海龙
传播学是什么?
刘海龙: 我想先提出这样的一个观点:我们很难通过简单的方式去定义传播学。首先,我感觉大家对传播学还不是很了解。此外,很多人好像对这个学科还有一些误会:一是觉得传播没什么可学的,因为我们每天都在传播,每个人多多少少都知道如何传播。也有很多人认为:传播做得好或不好,其实跟天赋有关,它不需要学习。二是大家觉得传播学是实践性的、比较偏重“术”的层面。
我个人理解传播学还是属于社会科学的一部分,尽管它也有实践的一方面,但它本质上是理解人和人之间交往的规律、了解我们整个社会信息系统如何运行的一个比较规范化的知识体系。它会把我们日常所熟悉的一些传播的窍门、经验,用一种科学论证的方式呈现出来。传播学并不能够帮我们立刻变得“更会传播”,但它至少会先帮助我们从如何去理解传播、如何看到这个传播背后的规律入手,慢慢地来改变自己,改变我们的社会。
董晨宇: 我也认为我们很难用一句话说明白传播学的研究内容。这可能跟它本身的学术渊源有关。有一种说法认为:传播学更像是一个领域,而不是一个非常严整的学科。我自己是研究社交媒体的。很多人会说“社交媒体中人和人的关系有什么可研究的,我天天都在用微博、用微信、刷B站”。从规律上来讲,我有一个比方:很多人都会开车,但我们要做的是给开车的人画地图、设置交规。所有开车的人都会先去学驾照,但不是所有上网的人都先要去学社交媒体中的规律。所以我们的工作不仅从术的角度出发,告诉你怎么发朋友圈,而更多是去探寻发朋友圈背后的心理、社会的影响因素。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讲师董晨宇
传播学者面对热点事件的独特视角
董晨宇: 许多人会对传播学者面对热点事件的态度感到好奇。首先,我并不认为传播学者一定会在所有的社会问题上拥有比其他学术研究者或者普通公众更深的见解。我们更多是以传播学作为一个新的视角。我常跟学生说,传播学特别重要的一点是帮我们打开了一扇窗。传播学这扇窗并不一定比文学或社会学更高尚,它只不过是一个新的可能性。
从某些热点事件中,我特别关注的是作为一个媒介载体,例如所谓的朋友圈的截图是如何被广泛传递的。这背后是对于“可见性的意愿”的违背:我发了一个朋友圈,是给我朋友圈当中的好友来看的,但是截图打破了这种可见性的预期,它可以被传到更大的社会范围中去。近年来,此类截图的传播也造成了许多谣言的扩散。为什么我们更相信聊天截图?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我们在偷窥一些内部的谈话。这些非常典型的人际交往,被转化成了一种大众传播的形式,插上了大众广泛传播的翅膀。作为一个社交媒体研究者,我不会仅仅关注某一事件,而是更关注聊天截图、朋友圈截图是如何改变人际传播的模式的。这可能是传播学所赋予我的一些观察问题的新视角。
刘海龙: 最近我看到有一系列此类事件,把这些事联系在一起,就能看到刚才董晨宇讲的可见性的问题。在当今社会,每一个人实际上都变成了一个监控摄像头。过去我们的监控可能只能由媒体掌握;但今天,社交媒体和新媒体把每个人都变成了一个监控摄像机,不断地扫描自己所在的信息环境,关注一些自己觉得比较重要的事情。这就回到福柯当年讲的全景敞式监狱的概念。全景敞式监狱只有一个视角:在监狱的中间有一个代表权力的眼睛正在看着所有的人。而今天我们会发现,所有人在看着所有的人。这样的状态会把一些我们过去不太容易关注的事件一下子呈现在大众面前,过去在朋友圈,或在一个群体里面能看到的事件,突然变成了一个大众传播的事件。
在今天,因为监控的到来,因为大众凝视和观看时代的到来,过去传播中的语境问题已经坍塌且消失了。这意味着,本来我要对着几个人讲话,但现在,我不知道我会对着谁讲话,我甚至可能是对着所有人讲话。从这种比较宏观的、媒体是怎样改变我们的社会生活的视角出发,我们可以看到传播和媒介是如何发挥了作用。
传播理论的挑战与影响
刘海龙: 这些年来,传播媒介的更迭和新媒体的出现也对部分传播理论造成了冲击。传统的大众传播是一个从中心向边缘进行单向信息扩散的过程,少数人掌握着信息传播的权利,大多数人只是一个被动的接受者。今天,这个情况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首先,信息的生产者开始变得多元化了。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是一个被关注的传播者,这在过去是难以想象的。这直接导致了过去传播理论里所讨论的很多现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举例来说,过去是大众媒体在给公众设置议程,而今天的很多事件都不是由大众媒体最早发现,最早去设置的。这些事件可能是在新媒体上出现,然后大众媒体让这个信息进一步破圈、出圈,最后成为一个公共议题。所以,一些理论的具体表现会出现变化。但我们也不宜把过去的理论全部推翻。因为不管新媒体怎么发展,还是会有很多公共性的信息。大众媒体会消失,但是大众传播一定会存在。
我们刚才看到这些广泛传播的事件,就是一个大众传播。也有人将它们称为大众个人传播或者个人大众传播,这种称谓模糊了两个传播形式的界限。在我看来,原有的传播理论中解释大众传播规律的部分依然是有效的,只是它的边界可能需要进行重新的定义。比如说“沉默的螺旋”讲的就是大众媒体可能会对我们造成的压力。我们会看到大众媒体里面存在某种多数意见,如果我的意见跟它不一致,可能我就不太敢在公开场合表达我自己的见解。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过去大众媒体是比较强势的,媒体报道会成为压倒性的多数。今天反而会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出来,人们总归能在网上找到跟自己相近的那些意见。这就是所谓的茧房效应或者过滤泡效应,我只接触跟我一致的信息,哪怕这些信息它是小众的,但它也可以给我营造一个很小的参照环境,去抵抗大众的声音。
但是我们也看到现在网上经常会出现,两种意见极端的对抗极化现象。这是不是也意味着沉默的螺旋不再起作用了?从表面上看,确实是这样。但我个人的观点是:它其实是一个沉默螺旋,变成了两个位于两极的沉默螺旋。本质上依然是一个意见占了多数,这也导致大家变得越来越极端。过去的中间派现在选择了保持沉默。因此在我看来,尽管媒介形式发生了更迭,但一些基本的人性论断是没有变化的。原来这些理论中所描述的涉及到人性、涉及人和人之间交流方式的最底层逻辑并没有变化。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说这些理论过时了,是它的条件发生了变化。很多理论最后讲的就是最基础的关于人的论断、人性、人的基本的特征,而几十万年以来,人类在这些方面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董晨宇: 我的看法和刘海龙老师比较接近。从表面上看,我们一定会有变化,这是2004年所提出的web2.0给用户生产内容带来的一系列的变化。
美国学者Jeff Pooley说过:传播学者特别像是推着石头上山的西西弗斯,在每一个新的媒体或媒介形态出现之后,可能这个石头都要掉到山底下,需要我们重新再推一遍。我们推完了广播,电视来了;推完了互联网,元宇宙来了。我们不断地推新的东西,为什么我们还要去看福柯,去看吉登斯,还要回到那些经典,他们不是已经被我们推完了吗?媒介不都已经过时了吗?其背后问题在于:媒介会过时,但是它所阐述的一些更内核的问题不会过时。黄典林老师有一句话,“现象易朽,问题永生”,比如刚才刘海龙老师所说的人性,“沉默的螺旋”可能会被不断地改造,但群体压力对我们表达行为带来的影响是永远不会变的。
刘海龙: 我可以再举个例子,刚才讲到的议程设置可以一直推到柏拉图讲的洞穴寓言,那个问题2000多年前就提出来了,柏拉图的《对话录》,《裴多篇》里就讲到技术的影响。书写文字的发明者忒伍特跟塔穆斯王对话,塔穆斯说:你的文字怎么样改变人,它本质上没有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智慧,只是让我们有了更多的知识。它讨论的问题就是媒介怎样和人的认知产生关系。这些永恒性的话题,不会因媒介形态变化而变化。它是人类一直在关注的,和我们人的行动、人的思想切身相关的问题。

《社交媒体简史:从莎草纸到互联网》,中信出版社,2019年3月
人类的交往本能永恒存在
董晨宇: 虽然媒体形式改变得飞快,但真正重要的、能够永恒存在的,其实是人类的交往本能。我们在赞叹新媒体的时候,也会发现这些媒体一点都不新。宋代有一个小说《流红记》,一个秀才进京赶考,在宫门外遛弯,突然有一片叶子从宫门里面小溪流出来,他把叶子拿起来一看,是一首宫女写的特别幽怨的诗,他就另取别叶,回了一首诗放进小溪,因为小溪是环绕的,就回流进宫里。若干年之后,他发现新婚妻子的包裹里面藏着他回的叶子,冥冥之中“方知红叶是良媒”。你觉得这东西老吗?一点都不老,这不就是宋代的QQ漂流瓶吗?人类的交往欲望,会因为媒介不断地得到满足,从最早的纸,到广播,到电视,到视频,再到VR,再到所谓的元宇宙,它在不断接近我们面对面交往的状态。当我们没有元宇宙,只有纸的时候,人们也会尽力通过纸来去表达和满足他们的交往欲望。最早我们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期,庞贝古城的岩壁上会留下大家的聊天,比如你写“你好吗”,第二天有人看见了,就回一句。这不就是脸书的留言板吗?
任何一个媒介出现之后,它的推广者必然会说它将是不一样的,会跨越一个新的时代,会解决很多的问题。在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互联网早期就充满了这样的流行话语,到现在元宇宙也是一样的,我们会说元宇宙会解决什么样的问题。若干年之后,我们会发现元宇宙所改变的,可能远远不及人们对它的改造和改变。对于技术改变人性的程度,我们是可以打一个问号的。人类的交往欲望和交往需要是和人性本质息息相关的。传播学的研究技术虽然发展得很快,但人性中特别稳固的东西,将永远会是我关注的对象。
刘海龙: 刚才董晨宇说到了交往,人和人间的交往或者是不交往,是一个特别永恒的话题。但我们今天的社交媒体,会把其中的某一个点扩大,社交媒体建立的是一个连接的意识形态:你一定要和人建立连接,不然你会显得非常落后,或者很孤独、很不受欢迎,所以我们不断地关注着自己的粉丝数量,觉得连接的越多,说明生活质量越好,但也会出现一种情况:连接的越多,反而觉得越孤独。这是一种群体性孤独,大家会发现,太多的连接并没有解决我个人真正的交往问题,是一个很虚假的交往。在任何时代,真的好友就那么几个。在很多视频网站上,你可能看到视频有几十万、几百万的播放量,但真正能理解的就是少数人,那部分人给你的评论可能质量会更高。当你突破那个圈子之后,你会发现很多人的评论对你的促进是很小的。
所以有的时候不交往,也许会过得更充实。梭罗到瓦尔登湖去隐居的时候,看上去他跟整个世界暂时切断了联系,但你会发现他过得很充实。因为他跟自然,跟动物、植物,跟天气,跟他所看的那些书上的经典的作家建立了联系,他每天在思考,每天在想问题,他并不觉得寂寞或者孤独。在今天,那样的一个人,如果社交媒体上没有一个人关注他,他也不关注任何人,就会被认为是一个很孤独的、有病的人,是一个可能精神上存在问题的人。
今天的媒体,会把我们的某一些特征给无限地放大,比如人要和人交往的这种特征。但它会忽略掉,人在某种时候,是不需要交往的,或者说是需要保持孤独的。比如我们要写书或者是做某件事,我们一定是要在孤独状态下才能思考,才能反思。
董晨宇: 我听说过一个学术名词,叫无线缰绳(wireless leash),以前的奴隶是靠一个缰绳,让你去干活。现在,我们的微信难道不是一个无线缰绳吗?哪怕改成什么钉钉、飞书之类,依然是一个无线缰绳。此外,大量包含着非常积极的、热烈的、亲密关系的词语被挪用到互联网当中,被资本利用,已经完全丧失了原来的本意。直播中主播老说:家人们给我点点赞,但是主播会把自己的观众真的当家人吗?这有点像“通货膨胀”,我们表达情感的词语越来越不值钱,虽然觉得很热闹,但心里一想,其实很孤独。

《交往在云端:数字时代的人际关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1月
关于传播学的反思
董晨宇: 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传播学比以前更像是一门显学,很多人表示要学习传播学来提高自己的媒体素养。理论上来讲,传播学确实应该是更重要了。但就像我们开始时提到的,每个人都觉得这个东西它不需要学,我会用就可以了,我能够掌控它,这是媒体给人的一个最大的错觉。对此,我觉得今天的传播学要反思:传播学者有没有给大家提供一个容易理解的一个成果?就像刚才说到的南希·拜厄姆的《交往在云端》,这也许不是她最好的学术研究,但它是一个很好的讨论,能让大家去了解研究者们在做什么。我们需要反思,我们这个学科的普及是做得是不是还不够好。
刘海龙: 当然,首先要反思是不是研究做得不够好,有没有回答大家所关心的那些重要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过去在研究中的路径依赖,没有回到大众、回到公众中去。其次,是我们怎样去和公众对话,把我们的这些成果,以他们能理解的方式告诉他们,我觉得我们的科普做得可能还不够。之前我看到一个讲《娱乐至死》的一个视频,点击量非常高,但我点进去看了内容,发现硬伤还蛮多的。所以,我们还是任重道远。
另外,很多学者可能有一个误区,认为你只要把这个知识学会了,就一定能够使用得很好。知识和知识的应用是同等重要的两件事情。但我们从研究者的角度来讲,可能更强调说知识的生产、知识的理解。第二个误区是,我们觉得知识有用的话,一定会影响到每个人。这也不一定准确,哪怕你懂了很多知识,也未必能够做好传播。传播的实践、传播的应用和知识的生产是同等重要的。在学术界,我们往往可能会忽略这一点:这是两个概念。当然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不能去贬低“学”,还要“用”,学以致用。而这个过程不是任何老师能教你的,必须要靠自己去观察。
对于理论的学习,不能够简单地去背这些概念,而是要深入到它的脉络里面,回到它的语境,去看理论的提出者是怎么思考问题的,为什么会这么想?他想出来这个东西怎么去解决当时的问题。重要的是学习那套思维方法,而不单是学那套理论。这个学科有点吊诡,传播学是个实践性学科,按理说学完之后也应该会做,但是结果并非如此,所以这里面存在着一个学习技能(Training)和知识教育(education)的区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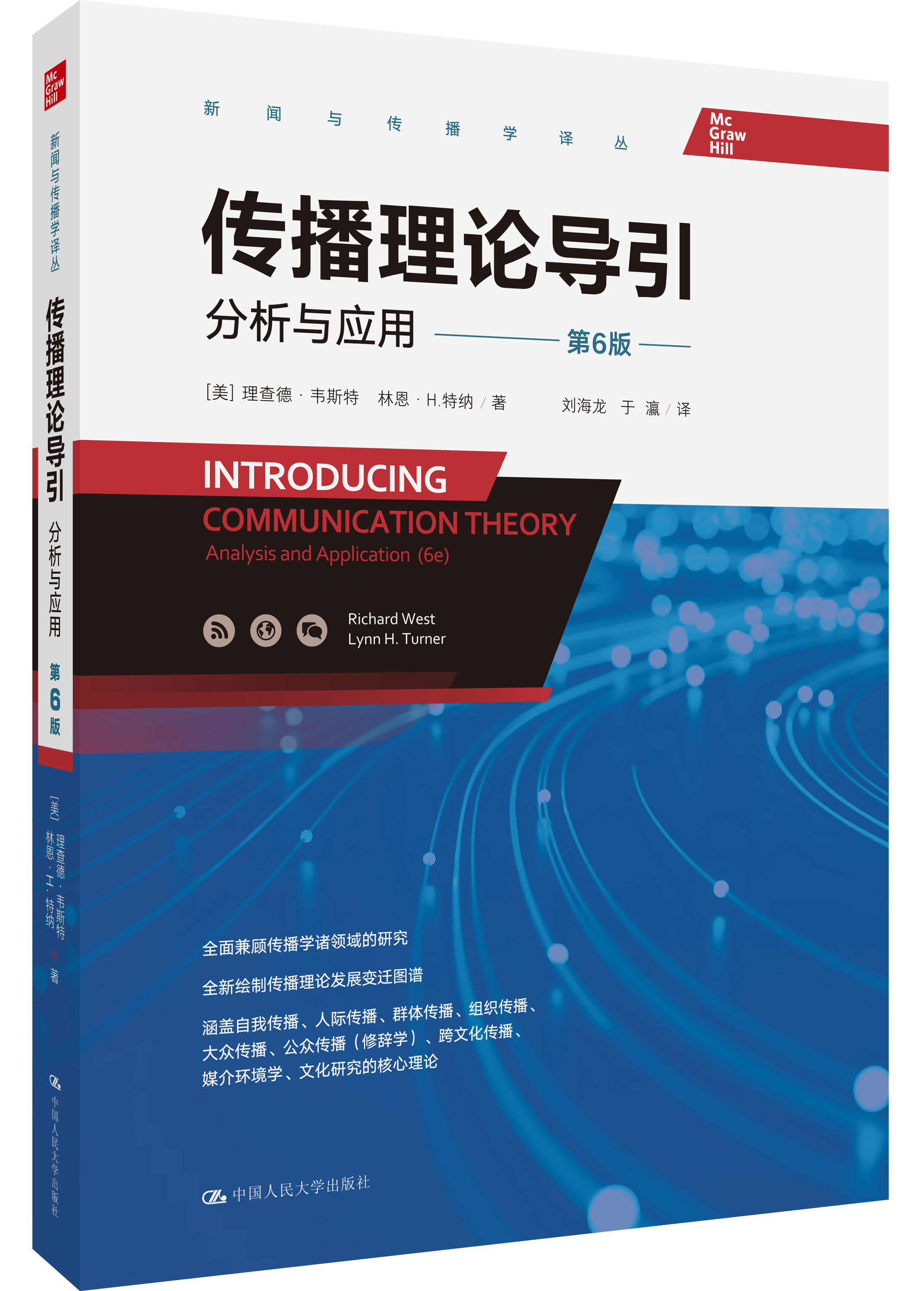
《传播理论导引:分析与应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2年3月
如何与经典对话
刘海龙: 在活动的最后,我也想向大一入学的同学推荐一些书目。这本新出的《传播理论导引》。它相对来讲比较好读,方便一年级学生学习导论,内容也比较简单。对于非专业的同学,会把一些基本的知识给大家讲清楚,让大家对于“传播学是什么”会有一个清晰的概念。
董晨宇: 我想推荐的是对我影响非常大的《社交媒体简史》它用非常故事化的口吻从古罗马一直介绍到现在,我们会发现搜索媒体、社交媒体根本不是现在才有的产物。从古罗马庞贝古城开始,一系列的媒介发展都孕育着人的交往本能,我们现在的技术不过是对这种本能的便捷化的满足和放大。这本书的结论可能并不重要,甚至我对它最后对社交媒体的展望有些失望。但是它给我一个很大启发:“太阳底下无新事”。当我们思考一个新的现象的时候,一定要把它放回到旧的脉络当中,回到像《传播理论导引》这样的教科书里早已说过那些事情中,我们会发现它在不断重复地发生。新事物并没有那么新,它在历史中早有暗线和伏笔,这也是传播学教我的一件事情。
另外,对社交媒体感兴趣的话,我前年翻译的《交往在云端》也是一本特别适合入门的书,这本书对研究者来说可能有点浅显,但它最珍贵的地方在于,最后的参考文献基本上把这个领域当中的经典基本都打捞了一遍。
传播学学子如何更好度过大学四年
董晨宇: 最后我也想给传播学的新生一些建议。社会学科给我的一个培养,或者说最大的帮助不是具体的理论,而是一种思维方式,一种社会科学的思维方式。首先,面对一个社会现象的时候,要明白“一切都不像第一眼看上去那么简单”,它并不是第一眼看上去的、浮于表面的那个东西。其次,是在你去评价(不管是赞美还是责备)之前,可能要去做一件事,那就是去问“何以至此?它为什么会变成这样”,这就是社会科学的一个思路。第三,就是它教给我社会科学的调研方法,不管是量化还是质化,这种思维方式会对我以后产生很重要的影响。人与人之间拉开距离的不仅是知识,还有理解和学习知识的能力,这是特别重要的。
刘海龙: 我刚才谈到,你学到的知识和怎样去使用你学到的知识,其中是有一定的距离的。但这是两件同样重要的两件事情。老师可能会主要集中在前一个部分,后一个部分实际上需要自己发挥主观能动性来解决。
大学给大家提供了四年试错的时间,可以做很多事情。比如可以去尝试做一下传统媒体,甚至也可以去广告公司,可以去新媒体,通过这种方式来找到最适合自己做的事情。传播是一个尴尬的学科,是一个更偏社会科学的方向,这使得它的就业去向不是特别明了。它会有一点点拧巴,这种拧巴导致大家好像什么都懂,什么都能做,但又好像什么都做不了。所以这也使得传播学本科专业方向的人可能会有一点点失落。但是我觉得,一是大家能够走学术这条路,二是可以学习其他的一些技能,比如视频的制作,或者通过统计学、通过大数据的分析方法去补上这一课。但这需要同学有更强的能动性。坐着干等,等着老师告诉你,你能做什么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除此之外,我还想补充一点。传播学这个专业,学或不学,它都在那个地方。今天没有任何一个学科能够逃过传播学的影响。比如文学,文学载体的改变其实就在改变着文学本身。我们今天的网络文学,包括其他的文学形态,整个的脉络其实都跟传播息息相关。包括金融专业,信息同样影响着比特币。甚至原来对我们来说很遥远的理工科,比如计算机,统计学,今天都在跟传播学不断的融合。其中一些影响了传播学,另一些则是传播学反过来影响它们。因此,无论大家是否在进行传播学的学习,传播学本身都是非常重要的。它对于我们了解、学习、做研究,思考自己专业的问题,都会提供非常多的借鉴和帮助。我也希望来自于不同专业的同学都可以来看一看传播学。
(周莹对本文亦有贡献)







